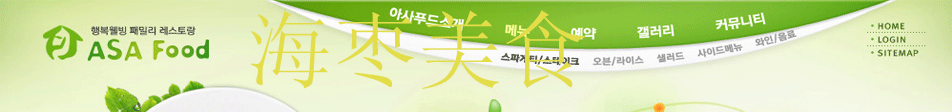|
战国秦长城东北端走向及相关遗存辨析 史党社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安,) 提要: 战国秦长城始筑于昭王三十五年(前年),从今甘肃临洮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北部一带,其西、北侧所面对的是匈奴与赵。对于战国秦长城的东北端,即在鄂尔多斯附近的部分,学界长期以来对其走向认识不清;对与此相联的赵长城的认定,也存在问题。综合传世文献、考古以及文字资料推测,秦昭王长城的最北端,应该只到达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部暖水村西,在此与战国赵长城相接,并非旧说所认为的走向东北十二连城附近。赵长城的走向,应从暖水村开始,向西北经过达拉特旗、东胜区,最终止于达拉特、杭锦旗黄河岸边,这里现存的东胜梁、新民堡-榆树壕战国长城,应属赵而非秦;东南则先转向纳林川西侧,再向准格尔旗东南、府谷方向延伸,止于府谷附近的黄河岸边,总的趋势应沿着暖水赵长城的走势向东南行进。秦、赵长城附近的广衍、西沟畔、福路塔等战国、秦汉遗存,其年代和性质也可由此得到更加清晰的说明。 关键词: 战国秦长城;赵长城;榆树壕;广衍;西沟畔;福路塔 一 序言 战国秦长城也称秦昭王长城,乃秦昭王三十五年(前)灭义渠后于始筑[1],比著名的秦始皇“万里长城”还早了半个世纪。后者是秦始皇三十三至三十四年(前-年)北逐匈奴出“河南地”以及黄河、阴山以北之后,在黄河、阳山(今乌拉特山)等区段新筑的基础上,连接原来的赵、燕长城而成的[2]。战国秦长城从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的洮河岸边开始,大致向东北延伸,经过甘肃定西、宁夏固原、甘肃庆阳、陕西延安和榆林市辖区,最后到达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陕西榆林北部的黄河岸边,长度约公里左右[3],所保卫的是秦西北边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战国秦长城从建立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年)秦驱逐匈奴出“河南地”[4],一直是秦之上郡、北地、陇西三郡的北部边界,界外为匈奴与赵之九原郡,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和族群意义。但战国秦长城东北端部分的走向至今仍不很明朗,还存在争议。本文欲对这一问题继续探讨,所牵涉的地域,主要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陕西榆林市北部一带。二 旧说存在的问题 在鄂尔多斯、榆林北部与战国秦长城相交织的,是战国赵长城。赵长城修筑于赵武灵王二十年(前)从林胡手中夺取“榆中”而设九原、云中等郡之后[5],现在阴山南麓的赵长城仍赫然耸立,俗称赵北长城,所保卫的是两郡北侧。在鄂尔多斯一带,即黄河南的赵九原郡西南侧,也有长城存在,与黄河之北的赵北长城构成一条完整的防线[6]。在地面长城之外,这条长城还利用了山、河之险,以及城池等形式[7]。辛德勇先生已经无可辩驳地论证过,这条长城就是战国赵长城[8]。战国秦长城从陕西神木南来进入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界内,此后的情况,诸论者的看法并不一致,观点粗略可分为三种:一种以史念海先生之说为代表,认为长城至于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边[9];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下称谭图)所示与史说大致相同[10];彭曦先生认为应稍靠西,其说与史说并无大的区别[11]。第二种以长城资源调查者为代表,认为战国秦长城止于今东胜北与达拉特旗交界的东胜梁一带[12];第三种为辛德勇先生的观点,他否定了史、彭等先生的十二连城等说法,认为战国秦长城应从暖水向东、经过点素脑包然后走向东南,至于赵九原郡南侧之南流黄河岸边[13]。鄙见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存在问题。第一种史、彭先生的观点,包括谭图的标注,都有个明显的误区,就是长城东北端若走向十二连城附近,都会经过九原、云中两郡的中部,造成两郡人为的分割,这完全不符合长城修筑的本意。因为长城是具有边界作用的系统工程,自应在边界地带穿行而不是境内。还有,纳林川的上源正川河作西北-东南走向,若长城走向十二连城,则一定会穿过正川河,此与下文将引的《水经注》记载相矛盾。第二种观点,根据新的长城资源调查,东胜梁长城,向西北明显通过山水之险,与达拉特旗的新民堡长城连为一体,向东南则达到暖水西,其应属于赵长城,保卫的是赵九原郡的西南侧,所以认为其为秦长城,是站不住脚的。第三种辛德勇先生的观点,虽然否定了传统流行之说,极富创建,但在这段的归属上,其说以并非无懈可击,原因是他对秦、赵势力在此转换过程的认识,存有一定的误差。近年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长城资源调查,加上研究的深入,现在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从准格尔旗暖水乡暖水村向西北至于达拉特旗的长城,属于赵长城;暖水以南走向神木的长城为秦长城。本文以此为基点将要讨论的,集中在暖水以东战国长城的有无、走向和归属等方面。三 战国秦长城东北端走向推测 (一)纳林川畔长城的有无及其归属当年史先生在准格尔旗界内亲眼看到的长城遗迹,集中在准格尔旗西部的准格尔召镇、暖水乡至于榆树壕(即史文中的巴龙梁长城)数段,暖水东北之德胜梁、坝梁长城,皆来自于当地人士之口,史先生并未亲睹,至于点素脑包,当时只是一高约3米、边宽2-3米略呈方形的土台,周围并无相连的墙体或山水之险,往北至十二连城,也无长城痕迹,史先生因此推测长城可能被漫漫黄沙所掩埋,北端亦应毁于黄河改道。不过,史先生对于暖水以东长城,还是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他曾亲观巴龙梁长城越过暖水川东去的迹象:巴龙梁东部逐渐低下,呈缓坡状,长城遗迹亦相应逐渐趋下,以越过暖水川。这段暖水川当是早已有之,故这里的长城遗迹随缓坡下降,直至川道深处,利用陡绝的深崖,补人工之所不及。越过这里的川道以后,再循坡而上,直攀上对面的梁头。隔川道遥望,清晰如绘。 根据史先生大作的这个导引,在暖水以东约略有赵长城的存在。史文中曾根据《水经注》,认为准格尔旗纳林川附近有长城存在,这给我们以重要启发。按《水经注》卷3云: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县,东南流……其水俗亦谓之为遄波水,东南流入长城东。咸水出长城西咸谷,东入湳水。湳水又东南,浑波水出西北穷谷,东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东迳西河富昌县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东流入于河[14]。 湳水即黄河支流纳林川,也称黄甫川(史文中称正川河),《水经注》记载其支流有二,一为咸水,一为浑波水,由这段记载可知,在湳水西侧近旁有长城的存在;长城并没有越过湳水向北或向东。纳林川上源,原来被认为是准格尔旗北部坝梁分水岭西的乌兰沟,其西侧有三条大的支流,一是黄甫川,今人也当作纳林川的正源,第二条支流为圪湫沟;第三条即最南面的一支是虎石川(也作什劳不齐沟),由暖水镇东南流出,至十字湾(也作石籽湾)村对面入纳林川。《水经注》中的咸水即圪湫沟,浑波水即虎石川。《水经注》说湳水西岸有长城,并且咸水的源头在长城之西,如果巴龙梁的长城越过暖水川,并到达湳水西侧,是完全可以满足“咸水出长城西”这个记载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湳水即纳林川的西侧有长城,如果肯定史先生的记述,即这条长城是从暖水川的西侧延伸而来的,则这条长城自应属于赵长城。这里出现了两个地名,一是美稷,一是富昌。美稷为西汉西河郡旧县,所置当在元朔四年(前年)设西河郡以后,汉设匈奴属国都尉于此[15]。对于美稷的位置,史文、谭图第二册第17-18页“并州、朔方刺史部”都认为即今纳林镇北的古城遗址。王兴锋最近提出,美稷所在当为暖水西北的榆树壕古城,其说有理可从[16]。榆树壕古城址位于榆树壕赵长城的东北(内)侧,时代上可至战国秦汉,后代不同历史时期曾加沿用[17]。从榆树壕古城的位置、门的朝向来看,与之紧邻的长城是向西南防御的,故应属赵长城。《水经注》说湳水出美稷县北而东南流,说的应是德胜北的黄甫川,源头正在美稷北。富昌的位置,按照《水经注》的记载,应在虎石川(浑波水)以下至于纳林川入黄处、纳林川的东侧,符合这个条件的,已知有四座城址,古城-前城[18]、郝家圪台[19]、沙坪[20]以及墙头乡冯家会古城[21]。其中的古城-前城古城,有“武都”陶文证明,其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武都县[22];沙坪、冯家会古城则规模太小,可当富昌者,只有郝家圪台古城。郝家圪台古城址呈长方形,东西边长米,南北边长米,规制足为一县,从时代和位置来看,与《水经注》的记载若合符节,故应即富昌所在。马孟龙认为郝家圪台古城应为战国秦汉的西都县,在《水经注》抵牾,故其说并不合理[23]。富昌的历史,可上推至战国。在战国文字资料中,有“富昌韩君”印[24]。李学勤[25]、曹锦炎[26]都把此印归属于赵,这是有理的看法。因为战国时三晋之中,韩国实力无论如何到达不了这里,也没有坚实的证据说明魏之上郡北界曾至于此,相反,赵在武灵王前后,势力辐射至此,却最有可能。印既属赵,富昌无论是邑还是县,就应为战国赵地,其上属只能是赵之九原郡。上文已经推测纳林川西侧有赵长城,由富昌的位置又可推测,这条长城应向南延伸,把富昌保卫起来。(二)战国-秦代纳林河谷历史形势的转换与长城的归属把纳林川东侧府谷郝家圪台古城认定为赵之富昌、古城镇一带为秦之武都所在,会导致两个不可回避的矛盾:一,战国时期赵之九原郡在北、秦之上郡在南,武都在秦至汉初属秦,更南的富昌却属赵,似与这个形势相左。二,武都在《汉书·地理志》中属五原郡,西汉中后期的五原郡承赵、秦之九原郡而来,以此推测武都当属赵之九原郡,但根据秦文字资料和张家山汉简可推测,秦至汉初的武都,却属秦之上郡。要解释这些矛盾,是非要弄清楚秦、赵、匈奴势力在此的转换不可的。陕北、鄂尔多斯东部地区,东周以来一直是三晋政治与文化的辐射区,魏、赵势力与白狄、胡-匈奴在此交织。秦在商鞅变法后,对东方三晋实行攻势,秦惠王十年(前年)夺魏上郡,势力开始到达陕北延安一带[27]。不过秦在本地区的扩张,是渐次进行的,其过程可简述于下:秦惠王后元三年(前年)夺魏平周[28]。平周在米脂一带,无定河的下游。秦惠王后九年(前年)又取赵之西都、中阳[29]。马孟龙论证中阳在今秃尾河流域的神木高家堡一带,位置比平周更加偏北[30]。秦昭王三年(前年),又置肤施于无定河中游榆林附近[31]。这应是为适应向东北扩张的趋势而设置新县。在秦昭王十二年(前年)以后又拥有准格尔旗西南的广衍[32],秦势力继续向北,到达窟野河上游、鄂尔多斯南部。随着秦势力的北进,上郡的北界也随之扩大,可是在拥有广衍这样靠北的县份之后,秦之势力却在纳林川附近止步,与赵形成对峙。其证一即上述富昌的存在,二是秦在此有武都县。秦文字中有数种“武都”的资料,年代最早的年发现于清水河县拐子上秦汉古城的武都矛[33],同出的纪年器铭最早者为秦王政三年(前年)所作矛,秦夺赵九原、云中,应在秦王政十三年前(前年),比此矛的铸造年代晚约十年[34],这说明秦有武都的年代,是早于秦有九原、云中两郡的时间的,此时的武都自然不属于九原,而应属于上郡。汉初张家山汉简中有武都县,根据前后文断之,也应属上郡[35]。新近公布的准格尔旗治薛家湾镇西南福路塔秦文化墓地M80所出陶扁壶上,有“武都当里”陶文,年代应在西汉前期[36]。从已知的“武都”文字资料来看,最早的武都矛的年代上限,应在秦王政初年前后,从此向前一直到秦有广衍(不晚于前年),大约有半世纪的时间,没有武都的任何记载,除却发现的偶然性,只能说明此时的武都并未设县,或未在秦手,这样就合理解决了上述两个矛盾:造成两个矛盾的原因,都是因为历史形势的转换。由武都南侧富昌的存在,推测纳林河谷应有长城存在,若赵对秦不设防,是讲不过去的。再看看赵势力在陕北、鄂尔多斯的消长。赵深入此地,至迟也在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辟土、置两郡、筑长城,都发生在赵武灵王二十年(前年)之后[37]。根据上文中阳的历史,可知早在“胡服骑射”之前,赵之势力已有涉足。辛德勇按照《史记》卷43《赵世家》武灵王二十六年(前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以及卷《匈奴列传》“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等记载分析,认为赵长城之修筑,就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38]。笔者鄙见,赵长城的修筑时间,应该更早,上限可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第二年,即赵武灵王二十年(前年),《赵世家》记载此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39],从此“榆中”附近的九原、云中就成为赵之领土,不然无法解释四年后所发生的移民事件。《水经注》卷3《河水》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前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40]若九原非赵地,则赵不可能迁民于此[41]。赵先行占领的云中、九原地区,迫使秦北进的势头停止而形成对峙的局面,双方的交界地区,由秦之广衍及赵之富昌的位置可推知,就在纳林川一带。秦文字资料中的“广衍”,最早的只到昭王十年(前年),并没有早过赵有云中、九原之地的武灵王二十年,也印证了赵先秦后的事实。这再一次说明,纳林川若有长城,也应属赵长城而非秦。这条长城从暖水西北而来,越过暖水川到达纳林川的西岸,向东南行进直到府谷界内的黄河岸边,从而把肥美的纳林河谷保卫起来。这种分布,与暖水川西的赵长城、窟野河西岸的秦长城极为相似,长城都是把河谷包于其内的。这个对峙的局面,大约延续了半世纪,至于秦始皇初年,纳林河谷的富昌被秦夺取;富昌更北的河谷,则出现了武都县,很可能秦在夺取纳林河谷之后,新设了武都,其上属为秦之上郡。不久,在秦王政十三年(前年),秦又向北完全夺取了云中、九原两郡。经过这两次变动,赵长城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武都、富昌在秦文字资料、张家山汉简以及《汉志》中归属的矛盾现象,原来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实地进行的长城资源调查所得资料,也支持这个推测。准格尔旗界内的长城遗存,在暖水西北,走向、修筑方式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现象。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所公布的暖水长城,被分为1段和2段,暖水长城1段以南区段向南与神木战国秦长城相接,诸家并无争议。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准格尔旗境内暖水西南的秦长城,总体还是呈西南-东北走向。可是,从暖水长城2段开始,长城的方向来了个大大的转折,折向西北而呈东南-西北走向,其向西北,与同位于暖水乡的榆树壕长城相接。不仅如此,从修筑方式来看,暖水长城1段西南以远的秦长城,多用石块砌筑;暖水2段以北长城,则以土筑为多,一直到达拉特旗新民堡长城都是如此[42]。我们知道,战国长城在秦末汉初曾经沿用,修补在所难免,但暖水南北方向两个区段的长城修筑方式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若仅以就地取材或后来修补去解释其因,恐怕是不够的。其中原因,当由修筑国家不同(赵、秦)、时代不同(赵先秦后)所造成。推测当秦势力到达于此时,赵之九原西南已经有了长城存在,秦只能退求其次,在赵长城南侧修筑长城,与赵、匈奴以长城为界而存在,暖水村西的暖水1、2段长城之间,当是战国赵、秦长城的交接点,也是分界点,暖水1段长城,就是战国秦长城的最东北端。总之,综合史先生文中记述、《水经注》、长城资料调查资料,以及赵、秦势力转换的历史背景,可以推测暖水西北的赵长城,应走向东南纳林川(皇甫川)的西侧,并向东南一直延伸到了府谷附近的黄河岸边,而非走向东北十二连城附近。战国秦长城的东北端,就应在准格尔旗暖水乡暖水村西北(见本文插图)。四 相关考古遗存的归属 国时期,陕北、鄂尔多斯一带由于长城的建立,本地呈现为赵、秦、匈奴三分的政治格局。本地东周秦汉考古遗存很多,明确了当时的历史形势和长城的走向,就可以对相关考古遗存的归属作出明确判断。本文将要说明的是广衍、西沟畔、福路塔。广衍位于准格尔旗西南纳日松镇、窟野河支流牛川上游瓦尔吐沟(旧称勿尔图沟)南岸,有城址、墓葬及相关遗物等发现,年代从战国到汉代[43]。广衍为秦上郡较偏北的一个县,西临秦昭王长城,北侧为赵长城,处于秦版图之内,所以文化面貌也以秦文化、汉文化为主,不见赵文化的因素。有学者认为广衍属于秦惠王前元十年(前年)魏纳秦的上郡十五县之一,忽视了秦上郡地域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当时秦之北境最远不过无定河流域,因此是不对的。杨宽等先生认为广衍为赵地,秦自赵得之,也不得考古资料的支持,从墓葬中存有北方畜牧文化因素来推测,广衍应是秦从畜牧族群手中开辟出来的土地[44]。西沟畔墓地位于准格尔旗西北布尔陶亥苏木西北7公里处,赵长城的内侧,年代进入战国-秦代的有3座墓[45],文化面貌畜牧色彩浓厚,与南侧的广衍墓地差异明显。尤其是M2中两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从上面的文字风格、衡制来分析,其当为秦所造;同出的银虎头节约上的文字风格却是赵式,器也是赵国少府所造[46]。M2的主人,应是归顺赵、秦的林胡之类,金饰牌与银虎头节约,都出自内地赵、秦对少数民族首领的赏赐[47]。战国时期此地先属赵而后归秦,所以出现了赵、秦两国的器物,推测虎头节约年代应稍早而银饰牌偏晚,后者当不早于秦王政十三年。福路塔墓地位于赵、秦云中(或九原郡)地域内,是近年公布的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存,发掘者认为墓地以秦文化为主体,年代大体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的主人多为秦人,这些秦人有的来自“西戎”,另外也可能有长城沿线北方民族的后裔。以上都是合理的认识,但发掘者对鄂尔多斯附近战国长城的认识稍显模糊,他们认为墓地在战国至于西汉早期,位于秦昭王长城内侧,不提赵长城[48]。鄙见认为,福路塔墓地与西沟畔墓地一样,都位于赵长城而非秦长城内侧,并且都经历了由赵而秦的政治变迁过程,但西沟畔墓地的主人,为先后归顺了赵、秦的北方游牧族群,畜牧文化色彩浓厚;福路塔则与广衍相似,有大量移民存在,故文化属中原系统。五 结语 战国秦长城东北端的走向问题,实际主要集中于准格尔旗、府谷一带战国长城的有无、走向和属性上。结合《水经注》等传世文献、实地考察资料、近年对相关县份位置定点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本地历史情势的重新分析,可以推测准格尔旗的赵长城,可能从暖水乡继续向南,沿着纳林川的西侧达到府谷附近的黄河岸边。相应地,建筑年代偏晚的战国秦长城,在从神木南来之后,东北端只能止于暖水西赵长城的近旁,而非传统认为的走向东北十二连城方向。这段长城存在了大概半个世纪,在秦夺赵之九原、云中之后即被废弃,这可能是其难以寻找的原因。本文的结论,自然存在推测的成分,希望以后能出现更多的证据来支撑。鄂尔多斯、榆林北部赵、秦长城及相关遗存位置关系示意图作者简介: 史党社(—),男,陕西省武功县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01期,引用请查阅原文!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子课题“秦国的崛起与秦统一” (1)《史记》卷《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1期,第1-51页。 (3)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年,第页。按此长度从彭曦说估计而来。彭曦认为战国秦长城长度约为公里,但其数据中有所谓南侧支线,对于这条支线的存在,笔者持怀疑态度,所以不全采纳彭说。 (4)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卷《匈奴列传》等文献。第-、-页。 (5)《史记》卷43《赵世家》、卷《匈奴列传》,第、页。 (6)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年,上册第-、下册第、页;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鄂尔多斯-乌海卷》,(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4、32-41、-、-页。 (7)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鄂尔多斯-乌海卷》,第32-33、40-41、-页。 (8)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年第1期,第15-33页。 (9)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年第1期,第16-22页。 (1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代“关中诸郡”,(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年,第5-6页。 (11)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页,第页图八十一。 (12)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鄂尔多斯-乌海卷》,第3、34页、第-页地图一“鄂尔多斯-乌海长城分布总图”。 (13)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第15-33页。 (14)杨守敬、熊会珍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15)《汉书》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刘玉印主编:《准格尔旗文物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年,第-页。 (16)王兴锋:《汉代美稷故城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年第1期,第-页。 (1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第页。 (1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年,第页。 (19)白茚俊:《陕北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61页。 (2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页;白茚俊:《陕北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研究》,第62页。 (2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第页;白茚俊:《陕北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研究》,第60页。 (22)吴荣曾:《武都城考》,吴著:《读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3)马孟龙:《西汉归德、中阳、西都地望新考——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年第2期,第59-66页。 (24)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第页。 (2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26)曹锦炎:《古玺通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页。李学勤与曹锦炎著作蒙责编提示,谨此致谢。 (27)《史记》,第页。 (28)《史记》卷44《魏世家》记载:“(魏襄王)十三年(前),张仪相魏……秦取我曲沃、平周。”《史记》,第页。学者们认为,《魏世家》所记秦取平周事,实际当为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前),而非魏襄王十三年。参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29)《史记》卷5《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后九年(前):“伐取赵中都、西阳。”另外卷43《赵世家》、卷15《年表》都有记载。《史记》第、、页。所谓“中都、西阳”,由张家山汉简可知其为中阳、西都的误写。周振鹤先生认为秦无西河郡,原来只能属上郡,并且当在黄河以西。吴镇峰先生根据汉墓题记,也认为在无定河中下游一带。参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73页;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年第1期,第45-49页;吴镇峰:《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年第1期,第53-69页。 (30)马孟龙:《西汉归德、中阳、西都地望新考——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为中心》。 (31)《水经注》卷3《河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体会《水经注》的文义,所言就是秦昭王三年置肤施,并且肤施还做过上郡治两层意思。《水经注》中所言“某年置”,应是初置之义。杨守敬、熊会珍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页。 (32)广衍县名,首见于十二年上郡守受戈。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年,第50-51页。 (33)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文物》年第8期,第63-64、76页;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1期,第54-58页。 (34)《水经注》卷3《河水》记载“秦始皇置九原郡”,又“秦始皇十三年,立云中郡”,云中与秦之间隔九原郡,秦夺赵九原郡,当不晚于此年。杨守敬、熊会珍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页。 (35)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第73页。 (36)胡春佰、格日勒图:《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发现秦文化墓地为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提供重要资料》,《中国文物报》年2月22日第8版。“武都”陶壶及文字见文中配图。 (37)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38)《史记》,第、页。 (39)《史记》,第页。 (40)杨守敬、熊会珍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页。 (41)杨宽先生即持此说。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页。 (42)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鄂尔多斯-乌海卷》,第20-41、-、-页。 (43)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第29、31-32、35页。 (44)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页。 (45)潘玲:《西沟畔汉代墓地四号墓的年纪及文化特征再探讨》,《华夏考古》年第2期,第68-74页。 (46)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年第7期,第1-10页,图版贰、叁;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年第7期,第13-17页。 (47)黄盛璋:《“匈奴相邦”印之国别、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年第8期,第67-82页。 (48)胡春佰、格日勒图:《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发现秦文化墓地为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提供重要资料》。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