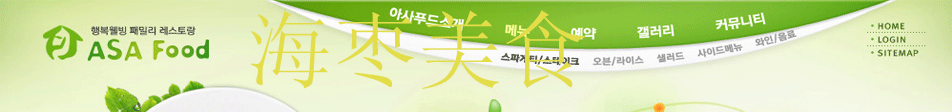|
白癜风治疗的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李永东 在国家象征与城市现代化的名义下,重庆形象的重塑为下江人的趣味和意愿所左右,“去四川化”与“上海化”同步进行,并因此造成下江人与重庆本地人主客权势的逆转。主客易势的权力状况决定了重庆形象主要由下江人的眼光与体验所建构,生发的故事为“下江人在战时重庆”的模式所垄断。下江人带着文化优越感、既有人际关系和他城经验进入重庆想象,他们“在而不属”的“重庆客”心态和体验,使得所塑造的重庆形象在时间上具有即时性、暂时性的特点,在空间上则着眼于城乡转换、空间分化的现象。 一、主客易势: 战时国都的“去四川化”与“上海化” 国府迁渝前以及抗战结束后,重庆是一个“在各种地图上都没有特别标记”[1]的内地城市。唯独全面抗战的八年,重庆作为战时国都,为世界所瞩目。年11月20日,当局宣布国府迁渝,重庆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由偏处西南的地方性城市变成了战时国都,四川人的重庆变成了全国人的重庆。正如重庆被定为陪都后《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所言:“现在的四川,已不是国家的‘边郡’,而是全国的襟领”,定重庆为陪都,“使全国感激兴奋,知道国家运命已与四川融而为一,而重庆尤必永远为国家胜利的象征”。“社评”还从国家层面对“重庆”进行了释名:“‘重庆’两字,就意味深长,我们将庆国家的胜利,更庆重庆的不朽!”[2] 重庆由地方城市升格为战时国都,不是一道命令就算完结。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恢宏建置”,“妥筹久远之规模”[3],自是必须。在精神文化上把重庆打造为“中国复兴的高垒,东亚改造的明灯”[4],也属当然。战时国都作为国家的象征,需要把现代国家观念嵌入城市空间和精神风貌的改造中,建成“民族形式的示范”[5],强化共同体的体认,赋予城市空间以政治中心的象征符号。张瑾的研究表明,国府迁渝后,国民政府通过多种举措来规范“新都”,具体措施包括:要求全市商店悬挂国旗,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推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运动,改变重庆的精神风貌;对街道进行重新命名(如:民权路、民生路、中华路、民国路、中山路、中正路、五四路),赋予其政治象征意义;打扫城市卫生,消灭老鼠。这是一场“自上而下”重塑战时国都的运动,蒋介石以各种手谕直接介入具体事务,从这个意义来说,张瑾认为战时重庆可谓“城市即国家”。[6] 战时重庆 战时重庆成为国家之城,就意味着其城市改造超越了地方传统和本地人意愿的规约,以城市的国家象征和现代化作为重塑的目标。挂国旗、重新命名街道、建造“精神堡垒”等空间建构,意在把国家的象征符号植入重庆的城市空间,以“城市即国家”来为国家抗战提供向心力和凝聚力。 当局以国家的名义对重庆的内外风貌进行规训、修改,也意味着“去四川化”,把重庆变成国人/下江人期待的模样。“下江人”是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长江流域各省的人心中的“下江人”概念在范围上有所不同。重庆人所使用的“下江”一词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下江人”则是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各省人的指称,甚至被用来泛称西南大后方以外其他省的人,正如张恨水所解释的:“四川则谓客籍者为下江人。其人苟不能操西方官话,(川滇黔)虽来自甘青,亦在下江之列。”[7]重庆城市形象的重塑,一定程度上为下江人的趣味和意愿所左右,“白布缠头”习俗的取缔即是典型例证。 众多下江文人都写到川人“白布缠头”的习俗,并把它看作是保守落后、有碍观瞻、不大吉利的一种装束。“居民保守性极重。天冷时不论男女,喜在头上箍一白布,习以为常,并不见忌”,相传此为三国遗风,“足见风气的闭塞,与受欧风影响的沿海各省,大不相同了”[8]。 “普通百姓,无论男女,头上都喜缠白布,就是不戴孝,也缠白布,有病更不用说。现在有碍观瞻,路中都被警察取缔,但在家或船上,还到处都是。”[9] 张恨水对于“白布缠头”的装扮亦多次叙及,他在《重庆旅感录》中写到川人喜欢以白布缠头,“俨然下江人在重孝中”,“唯国人旧习,最忌白色上头”[10]。到了次年的《重庆旅感录续篇》,张恨水仍不忘交代:川人以白布缠头,非常怪异,且用久了变黑,甚不雅观,“两年来,当局力纠正之,今行都市区,已鲜见此种现象。”[11]由此可见,下江人非但没有入乡随俗,反而把重庆的地方习俗看作是保守落后的表现,并以“国人”“当局”的名义加以纠正。“白布缠头”习俗的纠正,属于把西迁人群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愿,强行扭转重庆本地人的习俗以建构适合下江人的视觉环境,带有下江文化宰制重庆文化的色彩。其他方面同样如此,这些“大都来自通都大邑”的下江人,“教导了当地人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12]。在战时重庆,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惯例已然失效,主客权势发生了逆转,战时国都形象也由此得以建构。 张恨水 与“去四川化”同步进行的是战时重庆的“上海化”。“国都西移,以重庆为新都,苏浙人士增多,即成为上海式之重庆。”[13]“去四川化”是在国家的名义下对战重庆的规训,带有国家统合的政治色彩,旨在把地方城市改造为万众归心的国家之城。“上海化”则是下江人的习惯趣味在重庆的迁移与扩张,带有消费主义的色彩,体现出对西式、洋派的物质生活的迷恋。“上海化”进一步推动了下江人与重庆本地人主客权势的逆转,“客主之势既移,上下江之别,殆亦维持不易矣”。[14] 鄙夷当地文化,试图把当地改造成更加适合外来者的习惯喜好,而不大考虑重庆当地人的感受,这无疑是下江人与战时国家权力合谋的结果,应和了抗战建国的内在需要。这种现象是在国府迁渝以及江浙人西迁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只在战时国都发展成为一种显著的现象,在战时的昆明、贵阳、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后方城市,并不显著。 从战时人口内迁的方向来看,南京沦陷后,难民西迁的总体趋势为:南方苏皖浙赣鄂东的难民主要往西南迁徙,北方难民主要往西北迁徙。[15]从内迁人员的籍贯构成来看,战时重庆确实多江浙人。年重庆市居民籍贯统计显示,四川之外的其他各省居民约占重庆总人口的37%,主要为来自湖北、江苏、湖南、浙江四省的居民,其中江浙两省的居民占了迁渝人口的25%。[16]年12月的一份省籍统计资料则表明,重庆市的外省流离人员,以江苏和浙江为最多,占了流离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7]结合两份人口统计数据大致可推断出,流亡重庆的外省人中,江浙人在数量上占明显的优势。当然,江浙人的数量优势并不是重庆“上海化”的关键原由,因为迁渝的江浙籍居民不过占到总人口的10%左右,在数量上远不及四川本地居民。 重庆的“上海化”,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国府迁渝而来的公职人员,之前多生活在南京、上海,其生活方式、消费习惯都上海化了;二是上海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中心,随着高校、出版社、刊物、剧团、电影公司等文化机构迁渝,大批教师、作家、编辑、艺人来到重庆,带来了上海的文化趣味。而且,上海文化是欧化、时尚、现代、先锋的代名词,具有引领时代风潮的权威性,很快就在战时国都由一种新兴文化变成主导文化,变成下江人的集体文化形象。“上海化”不仅是人的转移,更是物质消费、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的转移。在服饰上,重庆本地“女人绝无高跟鞋皮鞋烫发等恶习,金兰布衫可谓全体一律。迄至战事起后,苏浙人士渐多,模仿时髦者始成为上海化”[18];在娱乐上,战时重庆“除跳舞场不准开设外,娱乐场所甚多,颇合下江人胃口,到处客满”[19];在商品方面,下江货“充溢重庆市上。市招飘展,不书南京,即书上海”[20]。各种上海元素的汇聚,使得重庆很快成了“大上海的缩影。除了没有洋鬼子底租界外,这里几乎应有尽有。不曾到过的人,总以为她是内地落伍的不堪想象的一个城市;但实情一经入他眼帘之后,他就要疑心他是置身于繁华的上海了”[21]。对于重庆本地人来说,他们最初“把重庆这新国都当作客人的政府”[22],熟悉的“我城”被下江人所改造,变成了令他们感到陌生的“他城”;对于下江人来说,上海的流行商品和消费空间大规模地挤进重庆的生活世界,陌生的“他城”就转换成了似曾相识的“我城”。 不过,重庆的“上海化”与共度时艰的民众心理和国家至上的抗战观念相龃龉。上海式的“洋派”“摩登”生活在战时重庆广受诟病,引发了爱国人士对“抗战司令台”的质疑。“上海化”一方面为下江人提供了仿拟的上海生活,安抚了下江人的离乡之愁,另一方面制造了川人与下江人之间的隔膜,通过服饰、消费、娱乐把社会阶层以醒目的方式标示出来;一方面带来了城市风貌的改观,赋予战时国都以应有的现代都市气象,另一方面有违节俭朴素、紧张严肃的战时生活,背离了大后方日益高涨的民主平等观念,不利于抗战精神的激发。例如在服饰上,“下面逃来的摩登太太和摩登小姐一多,无形中就把这都会的‘水准’普遍化了起来”[23],引起了一部分爱国人士的愤激。在《重庆二十四小时》《腐蚀》等作品中,怀念、沉迷上海繁华生活的都是国家意识淡薄、追求个人享乐的人物,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当局发布的消费禁令和执行的城市整顿,也包含了“去上海化”的意味,如在重庆严禁跳舞厅,禁销沪港厂制香烟,查封咖啡馆、夜花园,都涉及对上海式摩登浮华生活的约束。在文学中,对国都重庆的批判也包含了在消费、娱乐方面“去上海化”的意愿。沈浮的三幕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就直接对上海进行了祛魅。剧中的丁晓江、苏多丽流亡重庆却仍然眷恋上海的繁华,戏剧通过冯汉之口对“今日上海”进行了祛魅,指出沦陷后的上海只不过“千万种矛盾情感的挣扎,除去恐怖苦恼之外也就再没有什么了”[24],同时确认了战时国都的神圣价值:“无论租界也好,国外也好,最自由的还是站在自己的国旗底下!”[25] 在战时国都,“去四川化”与“去上海化”两种文化态度表面相悖,实则皆源于国家抗战的审视。“去四川化”是为了消除下江人对重庆的隔膜感,增强国家之城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去上海化”则是为了消除影响抗战的物质享乐观念,提倡艰苦严肃的抗战风气。国都重庆是“战时之物”,“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26],它的形象在下江人的战时人生插曲中被塑造。 二、下江人操控的重庆想象 “去四川化”“上海化”与“去上海化”,主要由下江人所引发,这也意味着下江人将在战时重庆的文学想象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也是如此。文学中的战时重庆,活跃的是下江人的身影,小说叙事几乎基于下江人的视角,戏剧演绎的几乎是下江人的故事。小说如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老舍的《鼓书艺人》,茅盾的《腐蚀》《过年》,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巴山夜雨》《傲霜花》《牛马走》,话剧如茅盾的《清明前后》,老舍的《面子问题》《残雾》《大地龙蛇》《归去来兮》等。就是那些题目中标明“重庆”的作品,讲述的也几乎为下江人的故事。“重庆二十四小时”的故事,并没有重庆本地人参与(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年的“重庆屋檐下”,住的是西迁的北平文人和上海掮客(徐昌霖《重庆屋檐下》);“新都花絮”飘荡的是京海趣味的闲愁与兴奋,呈现的是北平富贵小姐的多余人体验和乱世男女故事(端木蕻良《新都花絮》);“重庆小夜曲”的曲调不论激昂或哀婉,都属于流亡知识分子的咏叹(焦菊隐《重庆小夜曲》);“雾重庆”中只有雾是重庆的,经商发财或热心抗战的各类青年皆为下江人(宋之的《雾重庆》)。作品中的下江人往往有过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生活经历,主要人物曾经是同学、朋友、同事,他们带着既有身份与社会关系流亡到重庆。也就是说,许多作品讲述的是一群原本熟悉的下江人汇聚重庆后生发的故事,故事围绕下江人的熟人圈子展开,而重庆本地人则被排除在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之外。总之,重庆想象几乎被“下江人在战时重庆”的故事模式所垄断。 尽管移民占总人口的多数是现代大都市的常态,如民国时期的上海、天津、香港等,都主要由移居者和流动人口所组成。在作家的地域身份上,京派主要作家的祖籍不是北京,海派作家绝大部分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无论京派还是海派作家,多少都有点以城傲人的意思。就城市的同化力而言,北京、上海皆被称为“大染缸”,入京者或入海者,容易为其所化。新文学家即使对租界化的上海持“在而不属”的疏离态度,也不会着意突显自我的外省人身份。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的文学想象中,人物绝不会集体性地标榜自己的“外地人”身份,唯有在战时重庆,这种外地人/下江人的身份意识被刻意突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文学内外的人物,来到重庆最终是为了离开重庆,与重庆维持着貌合神离的暂时关系。按照张全之的说法,重庆是现代文学的“异乡”,作家打量这座城市的时候,体现了典型的“外地人心态”[27]。李南江年底打量重庆的心态,就很有代表性: “在北平,我爱在古柏森森的长安街上散步。寓居南京时,那长光荡荡的中山路,永远是我散步的地方。对于重庆的马路,严格说是小路,我只有望洋兴叹。也许是生疏罢?直到现在我对于重庆还是个陌生人。他不明白我,我也不明白他;谁也不想了解谁。”[28] 所谓重庆想象,实际上满纸皆是“重庆客”的战时际遇与家国感怀(司马的一部散文集的题目即为《重庆客》)。在重庆想象中,全面抗战初期“到重庆去”的热情逐渐消减后,下江人与城市的关系多了些勉强和无奈,显得你不情我不愿。每个下江人“说起对于重庆的印象都非常坏,几乎没有一个人说重庆好的,但是大家却都还耽在重庆,舍不得离开重庆,每个人对于重庆都好像有点留恋”[29],这是为何?《重庆屋檐下》中的文学家沙宗文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总的方面说,因为重庆究竟是抗战的首都,所以大家心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或多或少对重庆有一种敬仰爱恋的心情”,细加追究,每个行业的人留恋重庆的原因有所不同,但谋生的需要无疑是一个重要动因。[30]下江人留在重庆,是出于国家意识与现实生存需要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在张恨水、老舍、茅盾、宋之的、郭沫若、司马等的重庆想象中,那些汲汲于战时生存的下江人的重庆体验与际遇,仿佛车站滞留的旅客,或者交易所的投机者,充溢着颓丧、迷惘、兴奋、疯狂、挣扎、不安落、不甘心等情绪,怀着一颗随时离开的心,生活在别处。 下江人与重庆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下江人把重庆人在内的四川人“当作特别种类的次等角色”,而重庆本地人则“把下江人当作闯入者和外国人,应该加以处罚,榨取和讥笑,外江人来得多,物价高涨,这激怒了他们”[31]。下江人与重庆人的隔膜,不仅缘于语言、习俗、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也包括双方有意造成的固守与区分。在生活空间上,下江人与重庆本地人有所区隔。重庆沿江码头的角落挤挤挨挨的棚屋大半寄居着本地的苦力,他们的生活是“现实的地狱”,“对江南岸山顶上一座一座的小洋房,盖得美仑美奂,大半是外人的住屋,这些是另外的天堂”[32]。抗战前重庆上半城与下半城的空间对照与贫富差别,在抗战时转化为下江人与本地人的差距。即使共处移动的轮船空间,下江人与重庆本地人也自动选择了区隔,茅盾《船上》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不知是根据了什么习惯法呢还是各人的喜欢,本地人——特别是挑担子的乡下人总都在下舱,下江佬通常是直奔上层舱,这和下舱除了是在上面而且光线好些,此外实在没有什么两样;自然也比较通风些,可是煤灰也够你受”[33]。 下江人不大欣赏重庆的地方文化趣味。高绍聪谈到重庆的娱乐时写到: “川戏仅本地人听之不厌,像我们去听,演角唱词,好像念经,也不会武工,好角先做,也没有正本,没有什么兴趣”[34]。 下江人与重庆人之间的区隔和隔膜,不利于全民同心抗战的大局,以致重庆卫戍总司令在陪都成立大会上,要特意强调“打破地域观念,爱护他人”[35]。 下江人与重庆人的区隔和隔膜,隐含着下江人的文化优越感。下江人眼中的重庆人是鄙陋的,甚至带有蛮荒的色彩,因而需要按照下江人的观念加以改造。根据何鸿钧的口述,在国府迁渝的初期,下江人对重庆多怀有文化上的偏见,当年他就亲身经历了复旦大学下江学生与本地同学因习俗差异引发的“沿海较高文明与内陆落后文化之间的冲突”。[36]李南江年底对于“重庆一瞥”,关于重庆本地人的印象就是闭塞、保守,比下江人狭隘,“头脑不活泼”。[37]这种看法与小说、戏剧等虚构作品中的重庆人形象相呼应。重庆故事中的重庆人多数属于被支使的帮佣、粗人。老舍《面子问题》中的两位重庆人分别为佟秘书家的厨娘和机关中的茶房,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的陈嫂是佣人,端木蕻良《新都花絮》中的老王是八小姐家的厨子,看来有些傻乎乎的。作品中的重庆人与下江人之间存在明显的雇佣、主从关系,在身份上不平等,缺乏真正的交流。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重庆人,由于下江人的闯入,租用了本地人的房屋,征用本地民众作为下人、苦力,主客关系发生了逆转。 在下江人所把控的重庆想象中,重庆本地人处于边缘、弱势、被掌控的位置。徐訏的短篇小说《春》[38]讲述的是报馆编辑杨先生和农家女董小姐的战时爱情故事。在两人的关系中,重庆本地的董小姐处于被动的位置,下江人杨先生则操控一切,包括董小姐的哥哥在抗日前线阵亡消息的传播。小店铺的重庆姑娘成了下江青年的路上风景,由山脚通向报社的枯燥路程,因重庆姑娘的存在而变得富有诗意和激情。店铺有了董小姐后,“一连三天,编辑部都是谈董小姐”[39]。杨先生与董小姐订婚后,店铺换了主人,又一个重庆姑娘出现,“这大概是等小刘的了”[40]。与重庆姑娘的爱情,成了缓解下江青年精神苦闷的清泉。 在重庆想象中,占人口多数的重庆本地人或四川人,很少进入作家创作的中心视野。除了陈瘦竹《声价》、萧红《山下》、徐《春》等少数作品,重庆想象亦不大涉及下江人与重庆本地人的关系问题。进入重庆故事的重庆本地人,多数只是陪衬角色。而极少数以重庆本地人为故事主角的作品,其主题往往指向国统区基层权力的腐败和地方劣绅的贪腐掠夺,如草明《南温泉的疯子》、田苗《互替的两船夫》、郭沫若《金刚坡下》等小说。而且,作品中的重庆本地人往往既不承担叙事者的功能,也不是观察人事的聚焦者。他们总是处于被叙述、被打量的位置。下江人重庆想象的操控,还体现在重庆叙事中频繁穿插下江人在北平、上海、南京、香港等城市所获得的经验和记忆,这些城市的经验和记忆被用来映照、评价他们的重庆生存。北平的求学经历、上海的摩登生活、香港的物质奇观,不仅规约了下江人在重庆的身份体认、家国意识和道德形象,而且决定了他们打量重庆的眼光,成了推进矛盾冲突和情节转换的重要元素。 他城经验嵌入重庆的想象中,由此生发出对苟且偷安、摩登享乐、家国之思等观念的审视评判。例如,香港在重庆故事中就有着结构人物关系、扭转情节发展的特殊作用。在重庆想象中,香港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形成了一种模式:最初,香港助长了重庆投机商的发财梦,到了故事的结尾,香港的订货出了意外,导致他们破产,他们的重庆人生由此从张狂的巅峰跌入了失意的谷底;同时,香港是重庆商人的花柳地或风流男女的出逃地。沙大千的一批货物被炸毁,袁主任、苔莉去香港逍遥的计划泡汤(宋之的《雾重庆》);乔绅的订单因香港沦陷而钱货两空,桃云、丁影秋捐款私奔香港的计划也成了泡影(老舍《归去来兮》);鹤丹经理几十万的货在日军轰炸香港中全完了,苏多丽痛惜的是她留在香港的宠物狗(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在重庆故事中,香港是助长下江人罪恶的遥远城市,又在情节发展中扮演惩治重庆罪恶的关键角色。这就意味着重庆故事的讲述,需要借助他城的话语力量来完成。正是在下江人与香港、上海、北平等城市的牵连中,重庆作为国家之城的形象得以建构。对于下江人而言,战时重庆既是异乡“他城”,又是国都“我城”,因此作家在创作中既以战时国家的名义审视重庆和下江人,又把下江人战前的上海、北平、南京城市经验嵌入重庆形象的构设中。战时国家观念、下江人视角、他城镜像中的重庆,其城市形象可以概括为“流亡者的国家之城”。 三、下江人的时空体验与重庆形象的建构 城市的文学构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谁来主导城市想象,以及想象的是谁的城市,这一点至关重要。既然“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我们通过人群看见城市”[41],那么,以何种人群作为城市的换喻,就决定了想象城市的方式以及城市最终呈现的样态。城市形象的构设,是人群与城市的时间、空间交汇的结果。下江文人操控了重庆想象,意味着文学中重庆的时间和空间样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江人群的主体感知。城市的时间、空间和人群相互映射,构设出为下江人眼光和体验所主导的重庆形象。 虽然战时重庆的下江人与本地人在话语权势上“主客易势”,下江人掌控了想象重庆的方式,但文本内外的下江人并不打算落地生根,也无法把自己的身心妥帖地安放在重庆的时空中。他们在兵荒马乱中流亡到战时国都重庆,怀着去留无定的心态暂居这座城市,由此,下江文人构设的重庆形象,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即时性和暂时感。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城市形象的书写,总会有一部分作品着意表现城市的历史嬗变,讲述较大时间长度的城市人生,如林语堂《京华烟云》、穆儒丐《北京》、老舍《骆驼祥子》、刘云若《春风回梦记》、茅盾《子夜》、师陀《结婚》、巴金《家》等。而下江人构设的战时重庆形象,却没有历史感,只有当下性,讲述的是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庆故事。在茅盾《腐蚀》、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徐昌霖《重庆屋檐下》、宋之的《雾重庆》、端木蕻良《新都花絮》、老舍《残雾》等小说和戏剧中,“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的年代”基本重合。 在重庆故事中,下江人过去累积的声望地位无法在这座城市加以复制和延续,战时重庆结算了他们过往的生活,许多人面临时间的重新开始。在话剧《雾重庆》中,流亡到重庆的林卷妤、沙大千、老艾等几位大学生,经济上已山穷水尽,来重庆之前的抗战激情、大学生身份被暂时搁置,他们的重庆时间是从计划开小饭馆开始的;赵肃流亡重庆前“在家乡办教育,已经做了科长了,倒也满走时的。谁知道逃到这儿来,东碰一鼻子灰,西碰一鼻子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这么捱下了”[42],为了生存,不得不委屈自己在小饭馆当跑堂。对于重庆故事中的下江人来说,个人的生存、社会的重组、抗战的局势等问题,既始料未及、充满不确定,又显得那么急迫和切要。与重庆的暂时性关系,使得下江人的怨愤和欲望的表达刻不容缓,将即时性的体验和感受倾注于重庆形象的构设中。与重庆故事时间的当下性相应,下江人的战时重庆生活大起大落,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尖锐,情节推进快速,家国意识凸显,呈现了躁动不安、正在重新整合的重庆社会。 宋之的《雾重庆》,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对重庆的即时书写,除了源于民族抗战是战时国都和下江人所面临的最紧要、最切己的现实问题之外,还与下江人去留无定的生存状态有关。战时国都重庆,既是下江人的收容之城,又是必定离开之地。下江人“为着抗战的关系,一时流寓来此,终久是要回到‘脚底下’(下江——笔者注)去的”[43]。尽管下江人终究要离开重庆,但战局难料,时间未定,因而他们很难有长远的打算,他们在重庆的关系、身份、财富、苦难或享乐,甚至婚姻,都是暂时的。在生命的“待定”状态下,他们汲汲于生存,“忙迫是生活”[44],只能抓住眼前的一切,却不免举棋不定、进退失据。茅盾的小说《委屈》中的张太太为春衣而发愁,买还是不买对她来说是个问题,张先生的工厂是否继续办下去也是个问题,难以预料的抗战局势使得他们的重庆时间处于延宕未定的境地: “要是说,非在这里过一辈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让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走,这就比什么都难受了。”[45] 张恨水的小说《纸醉金迷》写到“抗战夫人”这一现象,男女关系是临时的,商业投机风云变幻,暴富与破产有时只是一夜之间的事。钱歌川因为“年年有离去之意”[46],一直未下定决心好好维修风雨飘摇的住所。下江人身在重庆,却怀着“在而不属”的心态,“正所谓想来重庆,求天求地;到了重庆,怨天怨地;离开重庆,谢天谢地”[47]。战时重庆形象因而弥漫着“怨天怨地”的情绪,充斥着对特权、投机、物价、道德、天气、交通等问题的辩难,人与城处于“他不明白我,我也不明白他;谁也不想了解谁”[48]的疏离关系中。下江文人构设的重庆形象,在叙事空间的选择和组合上,同样有其特殊风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文学构型中,常常涉及叙事空间的转移和对照,如现代小说、电影中的上海想象,就常在租界与华界,上海与苏州,霓虹灯闪烁的高楼与昏暗逼仄的亭子间之间进行空间的转换和对比,空间恰当地显明了人物的阶层和身份,空间或作为阶级矛盾、殖民反抗的场所,或作为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表征。而在重庆想象中,人与空间的关系被纳入新的叙事结构和表意框架。重庆的空间叙事和表意,与下江人的空间境遇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的最初两年,下江人在重庆的经济境况尚可,多数也有能力、有机会在城区觅得居所。年初敌机开始轰炸宜昌时,重庆“一般有钱阶级的人们,为了趁先逃命起见,都逃到农村去了。而从战区避难来此的,恰好填满了那般逃命者底空房。”[49]下江人最初在重庆城区容身并不是很困难,因而对于空间权力和空间道德并不敏感,李南江《重庆的一瞥》()、沧一《重庆现状》()、张恨水《重庆旅感录》()等文对重庆形象的描绘,以满怀优越感的外乡眼光,叙述了重庆的都市繁华和当地陋习,以及衣食住行等状况。 但是,下江人在重庆城市空间的占位状况并非一直如此。随着西迁的下江人不断猛增,重庆市区不堪重负,加上敌机频繁轰炸,当局决定疏散市区人口,大量人口四散到郊区和乡间的疏散区、迁建区。流亡重庆的下江人“大都来自通都大邑,曾享受过相当舒适的生活”[50],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为知识阶级”。[51]活跃在重庆故事中的人物,也主要是这一类下江人,他们对空间的占位极为在意。根据资本原则或机构搬迁地点对重庆空间的重新分配,使得原本拥有都市经验、习惯和趣味的一部分下江人,被抛入重庆周边的乡镇空间。还有一部分人在“轰炸季”疏散到乡间,“雾季”又返回市区,过着城乡交替的生活。由此,城乡空间的转换构成了重庆叙事的基本模式,老舍《鼓书艺人》、茅盾《腐蚀》、张恨水《傲霜花》、端木蕻良《新都花絮》、焦菊隐《重庆小夜曲》、宋之的《雾重庆》皆通过城乡空间的转换作为情节推进、命运起落的核心要素,呈现了散落的、城乡互嵌的重庆形象。[52] 下江文人的城市空间书写,偶尔会叙及下江人与本地人空间占位的反差,凯礼就感叹重庆沿江码头的角落,挤挤挨挨的棚屋大半寄居着本地的苦力,他们的生活是“现实的地狱”,而“对江南岸山顶上一座一座的小洋房,盖得美仑美奂,大半是外人的住屋,这些是另外的天堂”[53]。不过,下江文人念兹在兹、叙述最多的,是战时重庆所造成的下江人内部的空间分化。在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傲霜花》中,开头两章便呈现了空间与身份的反差,同样是流亡重庆的下江人,戏子王玉莲一家住在城里的西式楼房里,享用着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各种昂贵物品,仅仅梳妆台上的各种高档化妆品,就像一个“化妆品展览会”,与她一起欢笑宴饮的投机商人,都穿着漂亮西装,却一脸的浮华俗气,而王玉莲中学的老师唐教授,精通英法德三国文字,却住在郊区矮小破败的茅草房里。城乡空间的对照,商人与教授生活境遇的反差,包含了下江文人对战时知识分子境遇的哀怜和自嘲。 流亡重庆的下江人原本属于都市里的中上阶层,在城市空间的占位上有着优势。但战时重庆“中产阶层部分的新陈代谢”[54],拉开了下江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和地位高低,再加上重庆公教人员身价的整体跌落,这就造成了下江人之间空间占位状况极不均衡。下江文人多数身处重庆郊区或村镇,生活窘迫,故对空间占位有深切的感受,他们在建构重庆形象时常常突出叙述空间的分化状况。文学对下江人与空间关系的审视,背后为一套战时国家的正义观念所映射。下江人与重庆空间的关系,是对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和颠倒,占有阔绰、洋派的城市空间的下江人往往在个人私德、抗战大义上受到诘难,而寄生郊区、乡村的落魄下江人则在才学、人格上闪现着光辉。 空间分化涉及到对知识价值、道德良序、家国伦理失范的哀叹,对投机、掠夺、享乐的“成功”人物的揭批。住所的位置、周边环境、内部装饰,空间中人物的衣装、消费品的档次,甚至香烟的品牌、菜品的用料、衣服的做工、钢笔的来路,在老舍、张恨水、茅盾等人的作品中,都会不厌其详地予以交代。如此叙述,主要不是为了确证下江人的文化观念或审美趣味。实际上,对下江人与空间、物质关系的叙述,最终都成了道德的隐喻。虽然下江文人对号称“精神堡垒”“亚灯塔”的战都重庆的各种乱象和堕落风气多有揭批,但对这座城市的各类空间和下江人的叙述态度,仍然秉持“救国之道德”[55]的立场,而且道德评价往往与经济境况直接对接。战时普遍贫困的生存状况,使得下江文人对于有违战时经济政策和“战时生活运动办法”[56]的行为,对于谋求暴利、追求享乐、消费洋货的人群,无不加以嘲讽。经济行为和经济地位在战时重庆被道德化,投机商人、走私司机、中饱私囊的官僚,以及寄生于他们的舞女、交际花、戏子,不仅私德败坏,公德亦有亏欠。《归去来兮》中的乔绅,《残雾》中的洗局长,《腐蚀》中的舜英,《清明前后》中的严干臣,《雾重庆》中的袁慕容等人物,毫无节操廉耻,追求金钱享乐,伤害良善,阻碍抗战。在《重庆小夜曲》中,重庆南岸半山腰的一栋小别墅里花天酒地的下江男女,对抗战毫无兴趣,收音机正在播报战局消息,易太太骂了一句:“真混蛋,整天放送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57]下江人的空间分化,也是经济境遇、道德状况的分化,个体命运的叙述由此通向了对重庆形象和抗战观念的表达。空间和物质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走私的还是本地产的,新的还是旧的,与周边环境协调还是冲突,都构成了道德隐喻的必要元素,其表意实现了向民族形式、抗战观念、家国意识、社会平等、知识价值等主题的挪移和扩展。德行与空间的反差,以及身份与空间的错位,最终固化为重庆形象的主要建构模式。 结语 卡尔维诺说:“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58]主客易势的权力状况,决定了战时重庆形象主要由作为“重庆客”的下江人的眼光与体验来建构,而重庆本地人的城市感觉与记忆,则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很少显露。关于故乡与国家、城市与乡村、个人生存与抗战需要的思考,都是基于下江人的身份位置,重庆想象几乎被下江人所把控,呈现的是下江人的国都体验、生活境况和精神动向。在“去四川化”“上海化”与“去上海化”的观念纠缠中,在上海、北平、南京生活记忆的强行参与中,战时重庆形象得以呈现,与之相关联的国家观念、抗战意识的表达也主要基于客居者、流亡者的战时体验。下江文人在作品中构设的重庆形象,受到下江人“在而不属”的时空体验的规约。即时性的重庆故事,与重庆的暂时性关系,乡村与城市交替的叙事结构,空间占位的分化及道德评价,从多个维度构成了下江文人笔下的重庆形象。我们审视战时重庆的文学构型和抗战观念的表达时,应当考虑是谁在主导城市想象,以及构设的是谁的城市,这有助于更理性地把握战时国都的人、城和文学的关系,以及重庆想象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形式构成。 注释 [1][22][26][31](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北京:新华出版社,年,第1页,第3页,第1页,第8页。 [2][4]《祝重庆陪都》,《大公报》年9月9日。 [3]《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重庆:重庆出 版社,年,第87页。 [5]铁生:《新生中的陪都》,《现代华侨》年第6、7期合刊,第33页。 [6][36]张瑾:《“新都”抑或“旧城”:抗战时期重庆的城市形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年第6期,第页,第页。 [7][10][14][20]张恨水:《重庆旅感录》,《旅行杂志》年第1期,第51页,第52页,第51页,第51页。 [8]凯礼:《巴蜀见闻录(一)》,《旅行杂志》年第4期,第50页。 [9][34]高绍聪:《陪都重庆素描》,《旅行杂志》年第2期,第7页,第11页。 [11]张恨水:《重庆旅感录续篇》,《旅行杂志》年第1期,第31页。 [12][50]吴大业:《物价继涨的经济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第9页,第9页。 [13][18][19]高绍聪:《重庆琐记》,《旅行杂志》年第4期,第3页,第4页,第4页。 [15]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年第2期,第96页。 [16]《重庆市居民户籍统计表(年)》,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重庆:重庆出版社,年,第20-21页。 [17]《重庆市流离人民异动调查表(年12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 会》,重庆:重庆出版社,年,第28—29页。 [23][24][49]沧一:《重庆现状》,《宇宙风》年第69期,第—页,第页,第页。 [24][25]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重庆:联友出版社,年,第页,第页。 [27]张全之:《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23页。 [28][37][48]李南江:《重庆的一瞥》,《益世周报》(昆明)年第12期,第页,第页,第页。 [29][30]徐昌霖:《重庆屋檐下》,重庆:说文社出版部,年,第页,第—页。 [32][53]凯礼:《巴蜀见闻录(三)》,《旅行杂志》年第4期,第页,第页。 [33]茅盾:《船上》,《茅盾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页。 [35]舒福蓉编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史料一组(重庆市档案)》,《档案史料与研究》年第1期,第22页。 [38]连载于年7月8日至15日《和平日报》第7版“和平副刊”。 [39][40]徐訏:《春》,《和平日报》年7月14日。 [41](美)理查德·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10页。 [42]宋之的:《雾重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第6页。 [43][46]味橄(钱歌川):《巴山夜雨》,《巴山随笔》,重庆:中华书局,年,第4页,第5页。 [44]子冈:《陪都文化风景》,《大公报》(桂林)年9月6日。 [45]茅盾:《委屈》,重庆:建国书店,年,第14页。 [47]味橄(钱歌川):《夏重庆》,《游丝集》,上海:中华书局,年,第47页。 [51]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重庆: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52]李永东:《乡村里的都市——城乡互嵌的战时国都与文学书写》,《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第16—21页。 [54]茅盾:《“雾重庆”拾零》,《茅盾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70页。 [55]《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东方杂志》年第6期,第60页。 [56]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重庆:重庆出版社,年,第—页。 [57]焦菊隐:《重庆小夜曲》,上海:中国文化事业社,年,第31页。 [58](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张密译:《看不见的城市》,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页。 △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