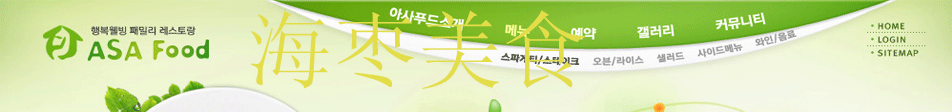|
东京光和书房收得近重真澄和神田喜一郎的旧藏,多有中国前辈学人的手泽,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国维的题跋本明版《大诰》和签赠本《壬癸集》《蒙古源流考》,《壬癸集》此前我已有专文记之。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签赠本,如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沈尹默《秋明集》、马君武《马君武诗稿》、顾廷龙《古匋文孴录》等。我已多次向吴忠铭兄预订这些书,情关割爱,迄无确复。因等不及,我便先为顾廷龙这本书写小记一篇。 《古匋文孴录》是顾廷龙先生的成名之作,他摹录字形并加以考释,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石印刊行,封面和扉页分别由马衡和王同愈题签,闻野鹤手书序,正文和自序由顾廷龙手书上版。“古匋文”即古陶器上的铭文,晚清收藏之风较前代更炽,青铜甲骨兴起之外,尚有古匋,陈介祺所藏最多,潘祖荫、吴大澂次之。而顾廷龙此著,所据资料主要来自周进、潘承厚两大藏家的拓片。周进是周馥之孙、周学熙之侄、周叔弢胞弟、周一良之叔,潘承厚为潘祖同之孙、潘祖荫侄孙、潘景郑之兄,都是财丰学厚的收藏世家。顾廷龙随周一良参观了周进的藏品,潘承厚则是顾廷龙的妻兄,但他们这些藏家虽多作拓件,对匋器尚缺乏整理研究,有之,则自顾廷龙此书始。 当时顾廷龙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这是应馆长洪业的邀请,具体负责图书采购。对于他这样一个嗜好藏古之人来说,这是最肥的“肥缺”了。所以当顾颉刚告知他洪业的邀请时,他极为兴奋。顾颉刚虽长顾廷龙11岁,却是他的族侄。其时顾颉刚准备研究尚书,邀他相助,具体参与《尚书文字合编》的研究工作。据沈津《顾廷龙年谱》:“顾颉刚与先生从事《尚书》之学时,正值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有《尚书正义定本》之纂辑,先生得与吉川幸次郎、平冈武夫等日本学者相往还。”这本《古匋文孴录》,顾廷龙以朱笔作大篆题赠:“善之先生教正廷龙中华民国廿五年七月。”“善之”为吉川幸次郎的字。 (吉川幸次郎签赠本)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于年至年留学北平,发出“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的感慨,以至于他在中国游历时,常被误当作中国人,而当他回日本后,有一段时间身穿中国长袍,以“贵国”称日本,以“我国”称中国。我在京都有幸收到他一些签赠本: 签赠平冈武夫《御题棉花图》满洲棉花协会康德四年(年)印刷(署“吉川幸次郎”) 签赠贝冢茂树《中国の知慧》新潮社年初版(署“幸次郎”) 签赠平冈武夫《中国と私》细川书店年初版(署“善之”) 签赠内田吟风《人间诗话》岩波书店年初版(署“善之”) 签赠青木正儿《陶渊明传》新潮社年初版(署“幸次郎”) 签赠平冈武夫《陶渊明传》新潮社年初版(署“善之”) 签赠青木正儿《西洋のなかの东洋》文艺春秋新社年初版(署“幸次郎”) 签赠贝冢茂树《吉川幸次郎讲演集》朝日新闻社年初版(署“幸次郎”) 日本循中国传统礼节,赠呈比自己年长或地位高者,应署名字;赠给同辈、晚辈或相好的友人,可署字号。不过也并非必然如此,比如吉川幸次郎和贝冢茂树就是同年。 此外,我还收得吉川幸次郎旧藏古籍一部,是康熙四十一年(年)席氏琴川书屋的写刻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扉页题记“癸亥岁仲春购于金阊席氏之肆”,钤“吉川幸读书记”。金阊在苏州,癸亥是年,其时吉川幸次郎虚岁二十。他晚年的《我的留学记》,专门写到上大学之前,到中国江南游历了二十多天,印象极佳,还特地感慨苏州的美女——“原来如此,竟有这么美的人”。时间地点都恰好契合,可知此书便是这次游历时的收获。此时他的书法还很稚嫩,与后来大相径庭,《我的留学记》写到他最佩服的中国学者是黄侃,他和黄侃笔谈,黄侃说他的笔意很“古”,还拿出一个扇面请他题字,多年后黄侃的弟子潘重规告诉他,此扇面黄侃至死都保存着。我有他两页手迹,是抄录琉璃厂来薰阁书店老板陈杭关于重刊日本藏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的跋文,信封却是陈杭亲笔寄与平冈武夫,题“内孝经跋文一页请校正”。年中日之间音讯断绝,他写了回忆文章《来薰琴阁书店——琉璃厂杂记》,直言:“陈济川,是我最想见的中国人之一。”他如此喜欢陈杭,想来陈杭那封信的原件,是被他向平冈武夫讨了去了,并工整誊录一份作为替换。 (吉川幸次郎旧藏康熙琴川书屋《唐诗百名家全集》) (吉川幸次郎誊抄来薰阁书店主人陈杭致平冈武夫函) 顾廷龙与吉川幸次郎的交谊后来还有续篇。《顾廷龙年谱》记载,年顾廷龙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日,12月8日晚刚到京都,便被告知吉川幸次郎、平冈武夫“均欲与先生相晤,先生闻之喜甚,夜不能寐”。11日,在正式接待宴会上见到吉川幸次郎,“见平冈先生,又见吉川先生,二十年未见之朋友,吉川赠《知非集》。宴会开始,吉川陪陶白座,平冈陪先生座。酒半,两人换座相陪。吉川告先生,已读完《元诗选》全部”。 可是,同为久别重逢,顾廷龙与平冈武夫的“契阔谈宴”却热闹密切得多。据《年谱》,12月9日,见平冈武夫,“午后至织锦厂,平冈先生在厂内相候,快获良晤”。10日,“出赴人文研究所,见平冈及所长森鹿三先生,又见薮内清、藤枝晃先生、小野和子女士、贝冢茂树夫人等。……平冈赠该所所藏目录二册,……晚观剧,平冈又来赠《文选索引》两册,并告先生五十年代与王煦华合作注释的《汉书选》,他买了六十册,即用作课本以授学生,并云此书较为重要。”11日,在正式接待宴会相见。12日晚,“八时平冈、小野夫妇及岛田来访”。13日上午顾廷龙离开京都。沈津《伏枥集》写到顾廷龙随团访日,配上了顾和平冈武夫二人坐在京都博物馆前石凳上的合影。综上可知,顾廷龙在京都,与平冈武夫频频见面,考虑到当时的外交禁忌,实在难能可贵。反观与吉川幸次郎的重逢,则显得寡淡多了。其实吉川幸次郎在一系列回忆文章中,也均未写到顾廷龙。 《顾廷龙年谱》记载,年3月20日,“访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出示林之奇《尚书全解》第卅四,丁杰校。此书前年在东来阁见过,因《通志堂经解》粤本已刊入,故未收,末附丁辑附录。今覆阅之,甚有用,即假归传录,深悔当时之不应放手也。又焦里堂批阎氏《尚书疏证》,余曾在富晋见过,索价廿余元,力不能办,既系为群玉购去转售他人,今又为平冈得矣。”书缘端的妙不可言!丁杰校本《尚书全解第三十四卷》和焦循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这两部书,有幸流转到区区在下手里,均有“平冈藏书之记”钤印,正是那一日顾廷龙艳羡平冈武夫的旧物。 (平冈武夫原藏丁杰校林之奇《尚书全解》阙卷) 丁杰即丁锦鸿,浙江归安人,是乾隆修四库时最重要的校雠官之一。因工作之便,他可将外界难见的珍本携出抄录,也常从琉璃厂借抄珍本以补四库。宋人林之奇的《尚书全解》第三十四卷“多方”久佚,丁杰从琉璃厂五柳居书肆看到,知是《永乐大典》本,遂借出抄校,连大名鼎鼎的刘台拱都凑了热闹。不过丁杰抄校之后,同仁争相借抄,致副本不下数十份。他第一手的抄本有亲笔跋文,今藏上海图书馆,我藏这一册,则是他的弟子金绍纶旧藏,有“丁杰之印”“大兴金氏绳斋藏书之印”“金绍纶读过”钤,抄录者手迹则与一手本完全一致,应为丁杰在首次抄校后再次誊录,而旁批为金绍伦笔迹。书后附订《附录》数页,署“归案丁杰辑”,钤“子山金氏手钞”,是金绍伦抄录丁杰之作,但楮间又有丁杰的数条旁批。可知此书的珍贵程度,殊不亚于上图所藏那一本。 焦循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则是康熙眷西堂原本。阎若璩是山西太原人,自小客居淮安,“眷西”者眷恋山西也,是他家的堂号。他用30年写出《古文尚书疏证》,此书一出,古文尚书之伪得到确证,故是尚书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焦循原藏及批校的这一套,为初印毛装,有焦循“焦氏藏书”“半九书塾”“焦循”“焦循阅”“理堂”钤,更难得的是有焦循的两处题跋和继藏者丹徒人庄棫的一处题跋。焦循题跋其一曰: “阎百诗之于《尚书》,惠定宇之于《易》,竭终身之力而为之者也。乃惠之《周易述》自‘升’以下全缺,其《易例》亦未成之书。百诗此作,一百廿八条,所缺二十九,吾不知两君更有何不暇而不自牢其业。甚矣学之难也。嘉庆戊寅十月初一日灯下里堂偶笔。” 其二曰: “嘉庆辛未八月中秋日里堂老人阅,是日雨无月。戊寅十月初七日灯下阅终,嫌其丛杂不成体。焦循里堂甫识。” (平冈武夫旧藏焦循批校题跋本康熙眷西堂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这些年游历京都,颇得平冈武夫旧藏,其中最值得
|